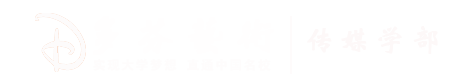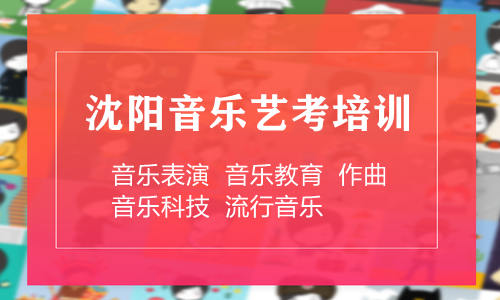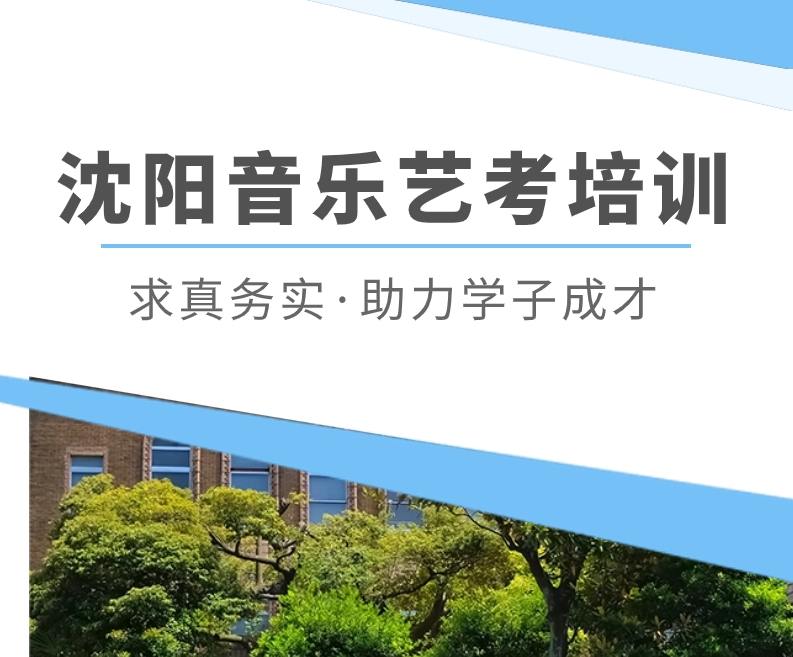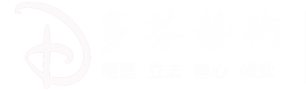- 最新艺考资讯
电影是浓缩的时空艺术也是永恒的时光印记,诚如《少年时代》浓缩了一整个青春也留住了一整个时代。回首那些银幕记忆中有多少雕刻时光的故事……
巴赞曾在《“完整电影”的神话》中说,在大多数电影先驱者的想象中,电影这个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象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幻景。当下,完整地再现甚至创造虚构的时空如梦境,已经成为电影在商业竞争中的不二法门,尤其当3D技术广泛地被应用于电影创作中,现实主义或者生活已经离电影越来越远,早已超越了巴赞对“完整电影”的寄寓。如今还有人能够用一年、两年甚至十年的时间去拍摄一部电影或者是纪录片,譬如《少年时代》,已经成为了奢侈与奇谈,殊不知这才是电影区别于其它艺术门类的宝贵之处。
塔科夫斯基曾将导演的艺术创作比喻为“雕刻时光”,而本文谈及的理查德·林克莱特、罗伯特·弗拉哈迪、弗朗索瓦·特吕弗与蔡明亮,可以说都是雕刻时光的“好工匠”。专注与执着是他们的风格标记,与演员之间长久而亲密的合作关系,也形成了银幕上一处亮眼的景观。有的导演与演员成为银幕内外的一体两面,甚至干脆打破银幕与现实的界限。他们在银幕前后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也成为了民族影像志的“少年时代”。
当速度与激情成为现代社会的虚像,观影心态由艺术审美转为用户体验,电影工业如庞大的机器高速运行轰隆向前时,让我们试图沉淀思绪,将这几段银幕上的“成长史”娓娓道来。其实,除了消费与娱乐,电影不应失去它最珍贵的品质——雕刻时光。
《少年时代》
3小时12年,时间就是现在
当《少年时代》在柏林电影节摘得最佳导演银熊奖时,国内评论界将所有目光都集中于金熊奖影片《白日焰火》上,但这并不能成为忽视这部“世纪钜作”的理由,将3小时交付于此片,会得到一种与后者截然不同的人生启示。它并非颓废而美,而是美而不颓。
上世纪90年代对美国独立电影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少年时代》的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也是这些独立电影人当中的一位。战后婴儿潮伴随着各种自由意识的熏陶,形成了他们与众不同的审美需求,米拉·麦克斯影业、圣丹斯电影节为他们提供了最佳的平台。90年代独立电影人明显的特质是具有作者性,编剧即是导演,他们并非科班出身,对于电影,完全出于个人的热情,因而他们的作品更倾向于风格化的个人表达。

童年的马森与父亲游戏
林克莱特最为中国影迷所熟知的就是他的“日落三部曲”,20年间3部作品启用同一对演员,不仅代他传递了关于爱情的箴言,也成了银幕上时光流转的奇观。同样,《少年时代》中的马森在近3个小时的银幕时光中,走过了他12年的人生历程,不得不说,这又是林克莱特酿制的一杯美酒。
马森的扮演者艾拉·科尔特兰在访谈中谈及,小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摄影机面向自己,因为导演让这一切看起来像是“一场游戏”,去表演化的台词与表演,使得这部剧情片更贴近生活。事实上,当你在暗暗惊呼每一处出其不意的时光转场时,不仅看到了马森的成长,也见证了他父母的老去。且不论导演点缀其间的时光道具,是如何慢慢引导观众陷入对往昔的追忆,例如第一代的台式苹果电脑、游戏机、手机、伊桑霍克的坐骑,又或是金曲大串烧的OST与“911”事件、棒球比赛、奥巴马竞选——标记般的为12年的时间线做时代提点。

成年的马森与父亲喝酒
马森与其他普通美国少年成长经历相似,却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在无技巧转场中,时间流逝得不着痕迹,但于生活的细微之处,母亲怅然若失的恸哭中,马森或者埃拉走完了整个少年时代。18岁是成年的开端,然而两个坐在荒野外的年轻人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永恒中,并非是我们把握时间,而是“moment sized us”(时间把握了我们),而时间就是此刻,是画面中两张年轻的脸,也是银幕前所有人的脸。
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几位导演与他们的作品序列,都具备独立的制作模式以及强烈的个人风格,并且在电影史上拥有无可取代的地位,几位导演的共同点则是专注于对同一个人物的长久刻画,从而记录了一个时代中的个体,也记录了这个时代。
《北方的纳努克》
一个史前的家庭生活录像
“史前生活”听起来或许有些夸张,但对照当下天马行空的现代生活,茹毛饮血的北极生活被称作“史前”也未尝不可。尽管电影中不乏描写史前生活的故事,然而纪录片之于时间的意义相较电影来说更加直接,它的真实性与时代性使得纪录片成为了时间凝固的容器,特别是一些具有文献价值的纪录片,不仅仅具有记录的作用,同样还保存了人类的智慧与文明。一部好的纪录片甚至可以说是一场生命与生命间的碰撞与交付,诗意动人。

纳努克一家“表演”晨起
1920年,一名到北方淘金不是很顺利的美国小伙子,竟疯狂地迷上了摄影机,他带着公司提供的充足胶片来到了因纽特人聚居的哈德逊湾,并且迅速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与纳努克一家——丈夫纳努克(Nanook),妻子娜拉(Nyla)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共同生活了16个月。通过纳努克,他认识了其它爱斯基摩人,并用摄像机记录下他们的生活,拍摄了这部被后世称为纪录片运动发轫之作的《北方的纳努克》,这个偏执而富有创造力的人正是被公认载入电影史册的纪录片大师——罗伯特·弗拉哈迪。
事实上,早在1916年,32岁的弗拉哈迪在替矿业公司到北极地带寻找金矿时,并没有发现大量金矿,但却找到了其他东西,其中就包括因纽特人的文明,他说,“这些人拥有地球上最少的资源,但却很快乐,他们是我所见过最快乐的人。”通过一架摄影机,弗拉哈迪拍下因纽特人的日常生活、仪式以及打猎的倾向。在与他们共同生活两年后,弗拉哈迪带着25000米底片回到多伦多。但一次意外,点燃烟蒂的火柴掉在这些底片上,马上化为灰烬,幸好他本人躲过了这场灾难。

对因纽特人日常生活的记录
1919年8月15日,不甘心的弗拉哈迪买了两架能在雪地里拍片的Akeley摄影机,带领摄影小组,再次回到哈德逊湾。这一次他打算回到因纽特人的身边重新开始。为了记载历史,他跟随因纽特人,记下他们生存奋斗的过程。“我希望,”弗拉哈迪在他的日记中解释,“以因纽特人能接受和了解的方式将影片放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我正在做什么,并希望他们能与我合作。
当我第一次带着所有的摄影器材抵达他们的住处时,他们十分惊讶,问我要做什么。我告诉他们打算在这里与他们共同生活一年,并拍摄一些有关他们日常生活的纪录片,他们大笑了起来。”通过当地一位从事巴黎皮草公司代理业务的法国朋友Duval 先生的介绍下,他去询问猎人纳努克——一位在这里很出名的性格人物,纳努克答应让弗拉哈迪于狩猎季节跟随他与同伴到海象岛去。

纳努克一家人陆续从一艘扁扁的皮划艇里出场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弗拉哈迪使用了大量长镜头,让人感觉不到摄影机的存在,他成了局外人,记录下纳努克一家是如何在冰天雪地中猎捕海象、搭建冰屋等等。事实上长镜头所创造出的远非记录时光流逝那么简单,它甚至可以制造惊奇。例如,在片子开始,纳努克划着一艘橡皮小船从画面远处缓缓靠来,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一叶方舟中,他竟相继拉出了全家人,甚至还有一只小雪橇犬。在另一个长镜头中,纳努克轻手轻脚地慢慢前行,镜头远远停在几公尺开外的雪地上,他逐渐靠近,突然弯下腰,半个身子探入一个完全没有被观众察觉的雪洞,不一会儿竟从里面抱出一只小狗。

纳努克用传统工具捕鱼的全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因纽特人在西方白人辈用过的鱼叉,真实地演绎捕杀海象,又花费很长时间搭建25英尺的超大冰屋“伊格鲁”,甚至因为采光不足在被削去一半的冰屋中表演晨起。尽管《北方的纳努克》曾因搬演的“真实”,掀起了一系列关于纪录片真实界限的大讨论,然而正是通过这种被弗拉哈迪称之为“积极干预”的长镜头与被拍摄对象所建立的长期相处方式,记录下了近乎与史前文明的人类生活,成为最早的民族影像志。
在拍摄与剪辑完成之后,弗拉哈迪决定在当地举办一场试映会,这是空前的创举。大约20个因纽特人挤在弗拉哈迪的小屋内,看着从黑暗中投射于床单上的一束灯光,当大家一眼认出画面上的海象,并随着纳努克的奋力捕捉而惊呼的时候,奇妙的故事开始了……
1922年6月11日,《北方的纳努克》在纽约首都剧场公映后便获得了很大的反响,人们从中感受到严酷的自然环境无法打击一个家庭艰难生存的乐观精神,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们反复观看这部片子的时候,除了被它的长镜头美学所吸引之外,还深深为这早已荡然无存的生活方式所着迷。正如弗拉哈迪在离开小岛时,指着身边河床上的石子,对纳努克说“会有像石子一样数不清的人看你的电影”。是的,纳努克一家确实在这凝固的时间容器中,年复一年地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安托万系列”
特吕弗的银幕分身
让-皮埃尔·利奥德14岁零5个月的时候,妈妈的朋友德·马奎斯推荐他去面试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在《法兰西晚报》上刊登的招聘广告是这样写的:“需要一个淘气调皮的12岁演员”。面试的时候,尽管自己比角色年龄大两岁,但是利奥德不加修饰的表演,不时引来导演的爽朗笑声。“我不像是爱思考的人”,“我昨天特意乘火车来这里,对我而言就像是渡假”,“生活中我是个快乐的人”,这些话并没有多么聪明,却让导演找到了银幕上的另一个自己。

孤独的叛逆少年安托万是特吕弗的银幕分身
毫无疑问,导演雇佣了他,当镜头定格在那个奔跑着的少年面孔上时,他成了新浪潮的代言人。此后的40年间他活跃于大银幕,其中最令人关注的便是他与这位导演合作的“托万系列”,说到这里想必早有人猜到,这位导演就是弗朗索瓦·特吕弗,二人一同开启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的作品,就是《四百击》。此后漫长的岁月中这对“精神伴侣”先后合作了十次,最著名的“安托万五部曲”包括:《四百击》、《二十岁的爱情》、《安托万和柯莱特》、《偷吻》、《床第风云》、《爱情狂奔》。
说安托万或者利奥德是特吕弗的银幕分身一点不为过。《四百击》中安托万的家庭环境来自于特吕弗真实生活经历。父母离婚后,十岁的特吕弗便与母亲和继父住在一起,两年后全家移居33 rue de Navarin二楼左首局促的公寓,特吕弗只能睡在置于通道的一张折叠小床上。安托万在学校是有名的问题学生,撒谎与造假,逃课看电影,体验真实生活,藐视权威,偷爸爸的打字机去卖等等,都是特吕弗少年时代的写照。1944年秋,某次被问为何旷课时,他广为人知的回答,15年后出现在安托万口中:“先生,我妈妈……死了……”

《安托万与柯莱特》中安托万搬到心仪的女孩家对面
青年时期的经历也都一点一滴地出现在电影中,《安托万与柯莱特》中搬到暗恋女孩子家对面住;《偷吻》中从精神病院被放出的军人要求提前复原;《日以继夜》中导演弗兰德梦到在夜深人静时,用螺丝刀拆掉影院橱窗玻璃,偷电影剧照卖,以及他右耳戴着的助听器(在现实军营训练中寒冷的天气与炮火轰鸣,造成了特吕弗终生右耳的听力问题),尽管这部片并不属于安托万系列,但利奥德扮演的导演身上依然有着浓浓的安托万影子。
很多人对安托万在少管所接受审问的那场戏印象深刻,事实上这是利奥德的自由发挥,对于推崇即兴发挥的特吕弗来说,利奥德的过人表现预示着他会是新浪潮的代言人。随后的拍摄中特吕弗鼓励利奥德自由发挥,从不否定他的灵感,“不要去考虑台词,要脱口而出”。谷克多在为《法国文学》写的文章里赞叹到“让-皮埃尔不假思索就完成了一项连最有才能的演员也不敢夸口的壮举”。

从《偷吻》到《床第风云》,夫妻关系已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如果说,《四百击》主要是特吕弗的半自传性个人表达,那么到了《偷吻》,“安托万的手势、态度、轶事甚至记忆都属于利奥德本人”。其中安托万在克里斯蒂家的酒窖中突然与她深情一吻的情节延续至《床第风云》,而此时二人已经结婚,与之前的小心翼翼相比,二人变得放松自然,但主动的一方换做克里斯蒂,推开对方的却是安托万。到了《爱情狂奔》中,安托万已经于银幕中经历了工作、恋爱、结婚与生子的人生阶段,但这些并没有成为叛逆浪子的桎梏,他依然在寻找爱与自由,甚至还出版了一本半自传性质的小说。
1979年“安托万系列”的最后一部《爱情狂奔》,也是利奥德与特吕弗合作的最后一部影片,它几乎是“安托万系列”的总结,我们看到了不同时代的他。特吕弗说,利奥德藉由安托万唤了心中那种恒久的感情:“一部电影完成后几个月,制片公司会同意销毁那些在最终剪辑没有被用上的负片。虽然对于我的其他电影,我乐意这样做,却不情愿如此对待整个安托万系列。我觉得利奥德的电影,像是冻结住了他成长中的不同阶段。”
在安托万与妻子克里斯蒂离婚的过程中,他回忆了他们相识相爱的片段,酒窖间的亲吻、睡前的小玩笑,甚至是婚后的大吵大闹,直至后来的和平分手。安托万的半生,浪漫却又一团糟。影片的最后,他巧遇儿时追求母亲的那位男子,后者早已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从他的口中安托万得知,母亲已于几年前离世。在老人的带领下,他来到母亲的墓地,母亲年轻的照片镶嵌在墓碑之上,而20年的时光已经于银幕内外消逝,安托万也在对往事追忆中,得到了人生的答案,那就是继续保持对爱的渴望与追求。于是,他奋不顾身地找到了心中的爱人,并向她表达了自己深藏许久的爱意。

不同时期的安托万(利奥德)
至此,“安托万系列”全部结束,而利奥德的银幕传奇却不限于此,他与戈达尔同样合作了不少影片,他是新浪潮两位“爸比”最爱的儿子。尽管在《中国姑娘》中,利奥德表现出激进的左翼身份,多少造成他与特吕弗之间的隔膜,但日后戈达尔与特吕弗渐行渐远时,利奥德成了连接俩人之间重要的桥梁。利奥德与特吕弗共同塑造的安托万形象不仅是银幕上又一“成长史”,同时也成为了无数电影人的心灵导师。当57岁的利奥德与陈湘琪坐在法国一所墓地旁的长凳上时,他再次与安托万重叠,这一幕出现在蔡明亮2001年的《你那边几点》中。接着我们就来说说中国银幕上的一段不可回避的“成长史”。
蔡明亮与小康的故事
不可回避的命运
2013年蔡明亮的《郊游》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导演的殊荣,与他合作了长达20年的李康生也首次摘得金马影帝桂冠。蔡导曾一度退出金马,表示不再参选,《郊游》则令他与金马冰释前嫌。
蔡明亮表示这是自己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部长片,今后他会将重心放在其它艺术创作上,不再拍摄长片(不过蔡导的食言是常常发生的)。也许《郊游》是这对“灵魂伴侣”在电影名利场中的完美收官,但在20年前的西门町电玩城门口,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两人的合作会一发不可收拾。蔡明亮的电影始终和一个名为小康的男子扯不开关系,他说,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灵魂伴侣”蔡导与小康
90年代初期的台湾社会已经开始转道,发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包括青少年犯罪,例如勒索、抢劫、艾滋病等等。1991年蔡明亮接到了电视片《小孩》的邀约,开始寻找演员,出演一个勒索小学生的高中生角色,一个“看起来不那么坏,可是他做了你也会相信的”。
面试了一连串的孩子,蔡明亮都不太满意,只好决定用文化大学戏剧系的学弟。谁知在开拍前一个礼拜,蔡明亮跟朋友跑去台大附近的公馆看大卫·林奇的《我心狂野》,电影结束后碰巧看到坐在摩托车上的李康生,当即向朋友表示“这个很像我要的人”,于是他走过去跟那个坐在摩托车上的青年说,“有没有兴趣拍戏?”,对方反应很久才回答“可以啊”。后来,这一幕被用在《河流》中,遇到困境的许鞍华,向在树下吃便当的小康发出拍戏邀请,只是并非找他出演主角,而是一具漂浮的死尸。
与小康合作的过程中,蔡明亮发现了他与众不同的节奏——比一般人慢了很多拍。渐渐地蔡明亮开始跟着小康的节奏走,也开始了他不为旁人所动的“小康的故事:“水”的三部曲:《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河流》,颇受法国艺术界青睐的《洞》、《不散》、《你那边几点》、《脸》,挑战台湾电检底线的《天边一朵云》,回到故乡马来西亚拍摄的《黑眼圈》,以及逼格更加高深的《郊游》与《西游》。每一个故事不尽相同,却又藕断丝连。
蔡明亮曾说,其实他最想拍的东西是时间,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数十年如一日的用相同的演员来拍摄看似关联的故事——李康生、陆奕静、陈湘琪、杨贵媚、陈昭荣……每一个人都成了蔡明亮镜头中标志。实际上,除了李康生之外,陆奕静也是从咖啡馆找来的“素人”,她瘦小精干,看似柔弱实则执拗,一口典型的台湾国语,正像极了每天出现在台北街头的普通女人。在蔡明亮的要求下,杨贵媚与陈昭荣这些职业演员们在镜头前脱掉表演的外壳,愈加接近真实生活中百无聊赖的人。陈湘琪除了参演蔡导的作品,其它时间都在台北艺术大学的戏剧系执教。

《青少年哪吒》中的小康与父亲
扮演小康父亲的演员苗天,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胡金铨镜头前的大侠,英雄与父权的象征,而在蔡明亮的片中,他隆起的肚子和日渐枯萎的肉身所呈现的,已不再是那个不可一世的英雄,而是个无法施教和与儿子乱伦的父亲。评论界常说“水的三部曲”到《你那边几点》是蔡明亮从“弑父”到“无父”的过程,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小康的父亲,是蔡明亮在有意识地对苗天几十年的银幕形象做“处心积虑”的颠覆,完成了对类型片中英雄与父亲的解构。
将电影建构梦境的规则打破,进而去表现近乎于真实时间的银幕时间,反映出了蔡明亮的艺术观——生活的平淡与重复。《你那边几点》与《脸》之后,无父无母的小康少了家庭的羁绊,他表现得更加洒脱,甚至更加挑战影迷们的底线,或许这就是蔡明亮从《金刚经》中所体悟出来的“行至本处”。因此,我们看到小康从一个瘦弱的叛逆青年,渐渐有了结实的身体,甚至用它操起了“皮肉生意”。
影片的时光流转则体现在万年不变的饭厅,越来越少的食物,永远摆着一张饭桌与桌子上由红到绿的电饭煲,还有一只游在泛着蓝光的水族箱中越来越大的热带鱼;永远在装修的台北与莫名其妙消逝了天桥;远景中小康孤独落寞的身形与中年男子成熟而坦然的脸。蔡明亮从不避讳自己缓慢的电影节奏,因此他的镜头并非通过场景的变迁来体现流逝感,而是在重复不变的场景与细微的变化中,回溯由内及外的物是人非,悄无声息地记录着时空流转。
半个世纪后的交错
雕刻时光的故事仍在继续……
上文中提及,让-皮埃尔·利奥德出现在《你那边几点》的结尾中,下面就要说道蔡明亮与特吕弗的不解之缘。蔡明亮跟着祖父祖母看邵氏电影长大,可是当他第一次在银幕上见识了特吕弗后,便成了“铁粉”,也从那时起,蔡明亮采取了毫不妥协的“反好莱坞”姿态,一次次地被排斥于工业之外,却又一次次地高居庙堂之上,几十年来欧洲电影节的奖几乎拿了个遍,却依然逃不脱票房毒药的称号。

小康看着《四百击》中的安托万,仿佛看到了自己
但细心的影迷一定会发现,蔡明亮大部分的艺术电影均有来自法国的投资,像《洞》、《你那边几点》、《脸》等等。其中,《脸》更是受法国卢浮宫之邀所拍摄,并且成为了第一部典藏于卢浮宫的电影。在《你那边几点》中,小康窝在黑暗卧室的一角,看着《四百击》中贴着墙壁旋转的安托万,表情由木讷转为注视。
影片近尾声的时候,陈湘琪却在法国偶遇了半个世纪后的安托万!那时她坐在长椅的一头翻找着什么东西,长椅另一头,一位留着齐耳短发的老者掏出纸笔写下自己的名字递给了她,从陈湘琪中文式的发音中,我们知道这个老人的名字——皮埃尔。有些观众此时才恍然大悟,这个人就是《四百击》中的少年“安托万”。这部电影中,蔡明亮用利奥德的现身对特吕弗做点到为止的致敬,而《脸》的全部灵感都来源于特吕弗。

年迈的利奥德
被认为是特吕弗最后一个亲密爱人的让娜·莫罗说道,“让-皮埃尔·利奥德、芬妮·阿尔丹、娜塔莉·贝伊,包括我,都在影片中扮演我们曾在特吕弗电影出演过的那些经典角色。片中,我一会儿是《朱尔与吉姆》中的‘凯瑟琳’;我一会儿又是《黑衣新娘》中的‘朱莉’。让-皮埃尔·利奥德饰演的则是一位极度想念特吕弗的演员。我们在一起,即兴创作,非常快乐。”
影片的结构采用元电影的叙事方法(一个导演拍摄电影的过程),这一次,李康生成了蔡明亮的分身,在布满镜子与雪的森林中,与有精神困扰的法国老牌影星利奥德坐在一起聊天。其间他们聊到了卓别林,也聊到了特吕弗,而这种戏中戏的剧情设置,直接对应了特吕弗与利奥德主演的另一部电影《日以继夜》。此时,正是双重的银幕时空与真实时空的互文呈现,相信于此场景中,一个特吕弗的影迷从中获得的快感,应该远远大于一个普通的电影观众,当然最过瘾的人莫过于在镜头后撮合这一切的蔡明亮。
不论蔡明亮与李康生的合作会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下去,毕竟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总有一天,我们会说蔡导与小康的故事开始走向尾声,但从观察世界的角度来看,他们仍像“刚刚开始”,始终保持着与社会的距离,但却一步步走入孤独人类的心里。
-
135687
-
95704
-
92196
-
91829
-
88858
-
87376
-
85509
-
83603
-
82488
-
81644

热门搜索: 广州多芬传媒艺考培训 广州影视表演艺考培训 广州摄影艺考培训 广东传媒艺考培训机构 广州编导培训机构 广州播音主持 广州传媒艺考培训学校 深圳传媒艺考培训机构

戏剧影视表演 播音主持艺术 影视配音
导演与表演 空中乘务 服装表演
播音主持双语播音 播音主持粤语播音
播音主持影视配音 播音主持商务礼仪
艺考培训服务地区广州市 深圳市 中山 惠州 佛山 东莞 清远 汕头 揭阳 梅州 河源 潮州 湛江 茂名 肇庆 云浮 江门 阳江 韶关 汕尾 珠海传媒艺考培训班 艺考大学招生
音乐艺考班 音乐表演班 钢琴表演班 声乐表演班 民乐表演班 录音艺术班 作曲艺考班 流行乐器演奏 流行演唱 音乐教育 音乐学 乐器修造 艺术管理
舞蹈艺考班 舞蹈表演 舞蹈编导
舞蹈教育 体育舞蹈 民族民间舞蹈
音乐考研班 传媒考研班 作曲考研班